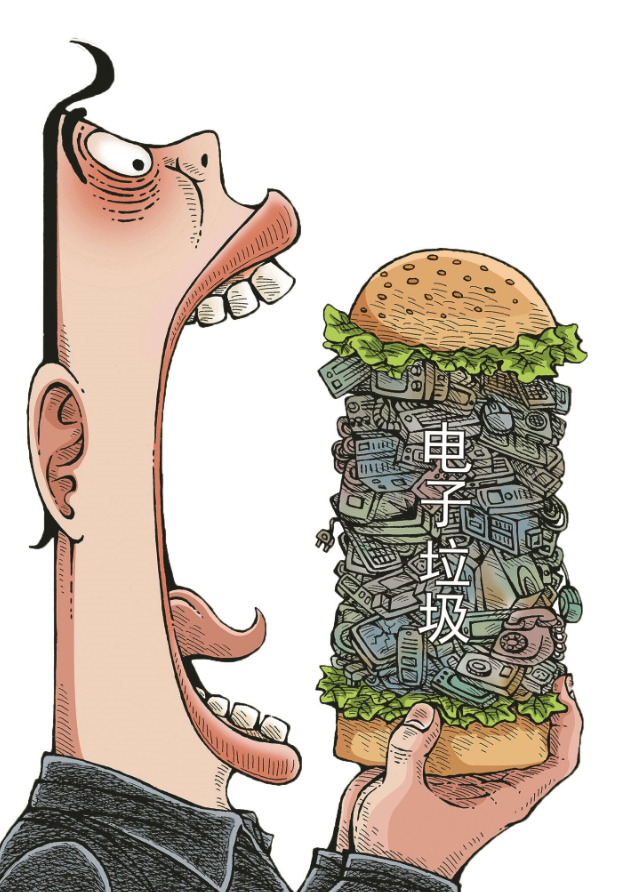“潘天寿是中国艺术传统的坚定传灯人,又是赋予现代变革精神的创造者。他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在战火迁徙中守护艺术教育的命脉,将‘博约弘毅’的校训融入血脉——即便在云南安江村的祠堂里,在重庆磐溪的黑院墙下,他仍坚持开设人体写生课、重建中国画分科教学,让民族艺术的火种在硝烟中得以延续。”
这是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许江在2024年12月31日宁海潘天寿艺术中心开馆仪式上的致辞,回顾并总结了潘天寿在抗战迁徙中坚守传统艺术教育、推动现代变革的历史功绩。

一
不易:四易校址,六易校长
1937年,那是一个被战火笼罩的年份,卢沟桥事变的枪声,如同划破夜空的惊雷,宣告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在这片饱受战火蹂躏的土地上,国立北平艺专与国立杭州艺专,这两所中国艺术教育的殿堂,也被迫卷入了时代的洪流,先后踏上了南迁之路。
国立北平艺专在校长赵太侔的带领下,师生们沿着平汉线匆匆南下,又转而沿长江而下,来到江西庐山。不久之后,他们又分成两批,向湖南进发,于 1937年11月、1938年1月先后到达湖南沅陵。与此同时,国立杭州艺专也在校长林风眠的率领下,于1937年11月底踏上了西迁的征程。他们先后抵达浙西诸暨县、江西贵溪、湖南长沙等地,于1938年2月间西迁至沅陵,与国立北平艺专的师生们会师。
两所艺专的合并,是中国艺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在沅陵老鸦溪,新成立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迅速建起简易的校舍,开始恢复教学。学校正式确立的“博约弘毅”校训成为国立艺专师生们共同的精神追求。然而,战争的局势愈发紧张。
1938年11月,日军攻占岳阳,进逼长沙。教育部下令国立艺专追随西南联大的脚步,迁校入滇。1939年元旦前后,国立艺专的师生们陆续抵达贵阳建起临时校舍。后因贵阳频繁遭遇日军飞机轰炸,艺专师生们旋即启程前往昆明。
1939年2月底,师生们陆续到达昆明,暂借昆华中学、昆华小学及圆通寺为临时校舍,再度复课。然而,昆明城也频繁遭受日机的空袭,为了保障师生的安全,学校再度另觅校址。当年12月,他们来到滇池东南岸呈贡县的安江村,国立艺专在此安顿下来,专注于教学和创作。
国立艺专在西迁途中,短短几年间六易校长,这一现象背后,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原因。
首任校长赵太侔,在国立北平艺专南迁的过程中,肩负起了领导的重任。然而,在南迁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他与部分师生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这些分歧逐渐激化,最终导致他不得不离职;
林风眠,在两校合并后,担任国立艺专的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他试图融合中西艺术教育理念,为学校带来新的发展方向。然而,由于两校师生在教学理念、地域文化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矛盾不断激化,学潮频频发生。林风眠最终不得不离开;
滕固接任校长后,致力于提高学术水准,树立笃实之学风。他为国立艺专制定了“博约弘毅”的校训。然而,长期的奔波和劳累,最终损害了他的健康。1940年,滕固与世长辞;
吕凤子接任校长后,他试图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来改善学校的教学秩序和提高管理体制。然而,迁校带来的办学条件艰苦,以及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让吕凤子积劳成疾,最终不得不上书辞职;
陈之佛接任校长后,事必躬亲,全身心地投入学校的管理和发展中。他积极延聘良师,改善教学条件,试图为师生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和工作环境。然而,时局的艰难,经费的短缺,仍然无法改变学校面临的困境,最终他也坚决辞职。
国立艺专在西迁途中,频繁的人事更迭,不仅反映了战争环境的极端不确定性,也暴露了艺术教育在动荡时局中的脆弱性。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学校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校长们不仅要应对战争带来的种种困难,还要协调师生之间的关系,解决教学和管理中的各种问题。
国立艺专在西迁途中的合并与迁徙,以及频繁更迭校长的经历,是中国艺术教育在抗战时期的一个缩影。这段历史,充满了艰辛与挑战,也展现了国立艺专师生们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对艺术教育的执着追求。他们在战火中坚守,在困境中前行,为中国艺术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4年,潘天寿临危受命,接替陈之佛出任国立艺专校长。
二
不弃:以学术为生命,以教育为天职
在那个战火纷飞、时局动荡的年代,国立艺专面临着诸多困境,而潘天寿以其坚定的信念、卓越的智慧和无私的奉献,肩负起了振兴学校的重任。他在《潘天寿论画笔录》中提到:“新,必须有基础,不是凭空而来。”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艺术创作中的重要原则:创新并非对传统的全盘否定,而是要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改造与发展。
为了提升学校的教学质量,潘天寿四处奔走,广纳贤才。他深知,优秀的教师是学校发展的关键。于是,他力邀林风眠、黄宾虹等名师重返学校任教。在潘天寿的努力下,国立艺专汇聚了一批国内顶尖的艺术人才,形成了强大的师资阵容。
潘天寿深知中国画教学体系的重要性,他致力于重建中国画教学体系,强调传统笔墨与现代精神的融合。
在教学中,他注重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引导学生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绘画的技法和理论。他强调诗书画印四全,提出人、山、花分科教学,首创书法篆刻专业,建构中国画的基础训练体系,为中国画教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坚持每周亲自批改学生作业,在重庆磐溪的三年间,共批注作业2300余件。其评语常以“强其骨”“重其气”为要,强调“民族艺术不可失却根本”。学生李霖灿(后任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在《艺术札记》中写道:“潘先生总穿着青布长衫,站在一尺多高的土台上授课。他教我们画石头,先示范用中锋勾轮廓,再用侧锋皴擦,边画边说‘画石要如铸铜打铁,笔笔见骨’”。

1944年,潘天寿出任国立艺专校长,离开云和前同国立英士大学艺术专修科师生合影留念
为了让学生们能够更好地学习和生活,潘天寿十分关注师生的生活条件。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他亲自协调菜油灯的配给问题,确保学生们在夜晚也能够有足够的光线进行学习。他还积极改善师生的住宿条件,为师生们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和舒适的学习环境。同时他又很强调因陋就简、因地制宜。
“血泪飞鼙鼓,江山泣鬼神。捷闻终有日,莫负储甘醇。”潘天寿先生西迁途中所作诗句,不言颠沛流离之苦,惟感神州陆沉之悲,道出山河兴复之志。正是因为有如此博大坚忍之心志,艺专师生才能够在漫漫西迁途中,维系住一个东西融合、古今贯通的艺术殿堂。

1944年,潘天寿与国立艺专师生在重庆磐溪
在潘天寿担任校长期间,国立艺专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危机。然而,他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成功地化解了一次次的危机。
在云南安江村办学时,国立艺专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人体模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村民们思想保守,对裸体模特存在着偏见和误解,认为这是不道德的行为。
然而,潘天寿深知人体写生对于美术教学的重要性,他坚持开设人体写生课。为此,潘天寿亲自深入村民家中,耐心地说服村民担任模特。他向村民们解释人体写生的意义和目的,消除他们的顾虑。同时,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祠堂修缮经费为承诺,邀请村民观摩教学;以表示对地方风俗的尊重。他用木板遮蔽祠堂神像,避免与村民的信仰发生冲突。
1945年,国立艺专又面临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学生罢课。当时,由于战争的影响,物资供应紧张,学生们对伙食质量十分不满,最终导致了集体罢课。潘天寿得知此事后,立即采取行动。
他亲自下厨试餐,亲身体验学生们的生活状况。他承认学校在管理上存在疏漏,并向学生们承诺会尽快改善供应情况。为了解决问题,潘天寿四处奔走,积极协调各方资源。他与供应商沟通,争取提高伙食质量;他还组织师生共同参与食堂的管理,提高食堂的运营效率。
在他的努力下,一周内协调军方配给,改善伙食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学生们也重新回到了课堂。他的这种敬业精神和对学生的关爱,赢得了师生们的尊敬和爱戴。
在他的领导下,国立艺专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与活力,为中国艺术教育的发展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人才。
三
不凡:潘天寿艺术与教育的双高峰
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潘天寿肩负着国立艺专校长的重任,却从未停下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的脚步。他以笔为剑,以墨为锋,在艺术的战场上,为抗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潘天寿创作了《焦土》《松鹰图》等作品,以独特的笔墨语言,描绘出山河破碎与壮丽的不同景色,寓意着国家的坚韧与不屈。画中的山川巍峨耸立,气势磅礴,仿佛在向世人展示着中华民族的顽强意志和不屈精神。同时,潘天寿还潜心于理论研究,撰写了《中国绘画史》。这部著作系统地梳理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脉络,从原始绘画传说一直讲到清末民初,介绍了24朝1600余位画家,分析了历代画家的画作创作背景、政治环境,各个画派的源流、传承演变、绘画特点,以及宋代之后历代宫廷画院的情况和名作。
这部著作不仅填补了当时中国绘画理论的空白,更为后人研究中国绘画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成为中国绘画理论的经典之作。潘天寿还积极组织师生在重庆举办“抗战艺术展”,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战争的残酷,激发了人们的抗日决心。

1938年潘天寿(前排右二)与李霖灿等学生摄于沅陵国立艺专大门
抗战胜利的曙光终于照亮了大地,国立艺专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他的努力下,国立艺专终于回到了杭州,恢复了西湖办学的传统。
回到杭州后,潘天寿致力于推动中国画的分科教学。他建立了“人物、山水、花鸟”专业体系,首创书法篆刻专业,为中国画教学构建了坚实的基础。他强调诗书画印四全,注重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引导学生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绘画的技法和理论。
在他的引领下,中国画教学逐渐走向专业化、系统化,培养了吴冠中、李震坚等大批优秀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潘天寿迎来了艺术创作与教育实践的新高峰。1959年,他再度出任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院长,同时兼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他1944年担任校长时首倡中国画分科,1959年担任校长时系统构建“人物、山水、花鸟”中国画教育的现代体系。在社会职务上,他先后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浙江省文联副主席,并连续三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艺术家的身份深度参与国家文化建设。
这一时期,他提出“中西绘画拉开距离”的著名论断,强调民族艺术的主体性,反对盲目西化,主张在传统笔墨精神中注入时代内涵。
在艺术创作上,潘天寿进入水墨画的巅峰阶段,代表作《鹰石山花图》《松鹰图》以雄强霸悍的笔力、奇崛险绝的构图,将传统花鸟画推向新的境界。这些画作1940年代构思,1960年代完稿,以焦墨技法象征民族劫难后的重生。
他的指墨技法臻于化境,手指、手掌、指甲兼用,所作荷叶如泼墨崩云,山石似铁骨铜枝,形成“强其骨”“重其气”的独特风格。理论著作《听天阁画谈随笔》《中国绘画史》等相继出版,系统梳理中国画的笔墨规律与美学精神,成为美术院校重要教材。
潘天寿的艺术成就被学术界视为“传统中国画现代化”的典范。他既恪守“笔墨当随时代”的古训,又突破明清以降的柔媚积习,将山水的雄浑与花鸟的灵秀熔于一炉,开创了“强雄静穆”的美学范式。
李可染评价其作品“笔力能扛鼎,在现代画家中罕见”,吴冠中称他是“传统绘画最临近而终未跨入现代的最后一位大师”。
1958年,他获颁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画家;1963年率中国书法代表团访问日本,推动东方艺术的国际对话,被誉为“东方艺术的使者”。
四
不忘:万峰最深处,饮水有生涯
中国美术学院的百年历程中,校名历经六次更迭:国立艺术院(1928)、国立杭州艺专(1930)、国立艺专(1938)、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1950)、浙江美术学院(1958)、中国美术学院(1993),共产生了十四任校长——林风眠(广东梅县)、滕固(江苏宝山)、吕凤子(江苏丹阳)、陈之佛(浙江慈溪)、潘天寿(浙江宁海)、汪日章(浙江奉化)、刘开渠(安徽萧县)、潘天寿(浙江宁海)、莫朴(江苏南京)、肖峰(江苏江都)、潘公凯(浙江宁海)、许江(福建福州)、高世名(山东潍坊)、余旭红(浙江开化)。
而围绕校长潘天寿形成三大独特现象,不仅是近400位“甬籍高校校长”群体中较为少见的,就是放在中国艺术教育史、中国教育史的视角来评价也是极为罕见的。
唯一两度掌校的校长:潘天寿于1944—1947年、1959—1967年在新旧中国两种制度体制下两度出任校长,其任期跨越抗战西迁与新中国建设两个关键时期,奠定了“传统出新”的教学体系。
唯一连续三任甬籍校长:潘天寿的前任陈之佛(宁波慈溪)于1942—1944年担任中国美术学院第四任院长,潘天寿后任汪日章(宁波奉化)于1947—1949年担任中国美术学院第六任院长,系潘天寿推荐,确保了学校西迁成果及相关工作的延续。中国美术学院自1941—1949年,前后三任校长均为宁波籍,形成“三任校长一脉相承”的地域文化奇观。
唯一父子同任同校校长:潘天寿之子潘公凯(宁波宁海)于1996—2001年出任中国美术学院第十一任院长,成为中国高等美术教育史上唯一父子相继的校长组合。
如今,在潘天寿的故乡宁波宁海,他的艺术精神已融入城市肌理,形成多层次纪念体系:潘天寿故居(宁海冠庄村)于1997年修缮开放,陈列潘天寿早年习作与生活实物,其“雷婆头峰寿者”的题刻与故居后山的自然风貌相互呼应,成为“画魂归处”的象征。2024年新近落成的潘天寿广场与艺术中心位于宁海县城中心的潘天寿广场(2007年建成),设置了潘天寿、潘公凯珍藏作品的常年展。
在教育领域,宁海城关设有以潘天寿姓名命名的“潘天寿中学”,学校将国画教学纳入校本课程,定期举办“小潘天寿”书画比赛,校园内立有潘天寿青铜像,基座刻其“强其骨”的艺术箴言;在宁波大学,2015年设立了以潘天寿姓名命名的“潘天寿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以潘天寿艺术教育思想为根基,开设“潘天寿奖学金”,2024年与中国美术学院联合培养研究生,形成“校地协同”的人才培养模式。这些纪念空间的设立,不仅是对潘天寿艺术成就的致敬,更将其“民族艺术不可失却根本”的理念转化为当代文化实践。
潘天寿晚年常以“雷婆头峰寿者”自喻,将自己比作故乡宁海的一块顽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于烟盒背面写下:“万峰最深处,饮水有生涯。”这句诗,既是他豁达心境的写照,也是其艺术教育生涯的注脚。
从烽火西迁到西湖重建,潘天寿以“艺者仁心”守护着民族文化的火种,他的名字,注定与国立艺专的历史同辉。他的故事,是中国艺术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在艺术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创新,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努力奋斗。特邀嘉宾 沙力 黄江伟/文 郁伟年/主编
编辑: 郭静纠错:171964650@qq.com

中国宁波网手机版

微信公众号














 如何打造AI高地?"最强智囊团"来宁波支招
如何打造AI高地?"最强智囊团"来宁波支招